所需要的只是一而再,再而三,无休无止地克服你自己的记忆。他们将其称为「现实控制」;用新话讲就是「双重思想」。
—— 乔治·奥威尔《1984》
出于几个原因,我于1979年出版了《变性帝国(The Transsexual Empire)》,这本书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发展而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女权主义者们发起的女性健康运动正蓬勃发展并向许多对女性有害的医疗实践发起有力挑战,例如非必要的子宫切除术就是被批判的实践之一 。
彼时我的大部分教学、写作和参与的社会活动都集中在批判那些破坏女性身心的医疗技术 —— 例如精神外科手术 (过去称为脑叶切除术) 和电击疗法等行为控制与矫正技术。早期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经历令我开始质疑跨性别手术无法规避身体部位损毁的医疗后果,以及终身服用荷尔蒙的有害影响。
尽管那时接受性别重置手术的大多是男性,但我怀疑变性主义(transsexualism)及其较为现代的变体 —— 跨性别主义(transgenderism)试图通过抹除女性身份改变女性生活,并给我们贴上听起来极为冒犯的标签。但没人预料到跨性别活动人士竟称我们为顺性别女性、TERF、前洞1 、子宫所有者、卵子生产者、母乳喂养者 —— 甚至是「非男性」—— 讽刺的是他们唯独将「女性」这一称呼留给自己。甚至堕胎服务提供者也选择屈服,将使命宣言中为「怀孕的女性」服务改成为「怀孕的人」服务。
《变性帝国》的部分书评者仅因标题含有「帝国」一词便称我为阴谋论者。我采纳这个标题的目的是将由跨性别咨询、手术和荷尔蒙治疗构成的社会性别产业置于聚光灯下。该产业调动大量普外科、整形外科、内分秘、妇科、泌尿科,和精神科医生来确保自我认同为跨性别的个体能「转变」到渴望的生理性别,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顺应父权制下的生理性别角色(sex-role)2。
那时我在《变性帝国》中提到,对社会性别不满的医疗化如今呈现指数级扩张趋势,成为建立在大型医疗机构、制药公司、银行、基金会和一些大学附属的大型研究中心之上的社会性别认同工业复合体。像乔治·索罗斯和詹妮弗·普利兹克这样资金雄厚的资方为跨性别运动提供海量资源,并协助出资构建起庞大的运作体系,从而让跨性别主义在立法和政策制定中具备影响力。尽管跨性别者数量较小,但它并非一场缺乏资金支持的边缘运动,而是一场在许多国家推动跨性别意识形态和实践合法化,资金充裕的全球性运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跨性别活动人士开始挑战女权主义者的主张 —— 即跨性别主义鼓励人们重新扮演保守的生理性别角色。相反,他们主张跨性别主义是对社会性别的挑战。此外,专业术语也由变性主义改为跨性别主义。跨性别支持者称,正是跨性别者而非女权主义者对社会性别提出激进挑战,通过接受承诺构建外观相似的异性身体的荷尔蒙治疗和手术,跨性别者不仅超越社会性别期待,更打破了二元生理性别角色的僵化界限。
时间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跨性别活动人士开始通过声明自我性别身份认同直接获得渴望的男性或女性身份,手术和/或荷尔蒙治疗不再是转变的必要条件。
人们时常向我提出两个问题:「跨性别议题值得这么大动干戈吗?」和「为什么跨性别问题在女权主义者面临的众多紧迫议题中显得格外重要?」 在我当时以及现在看来,变性主义和跨性别主义提出社会性别是什么以及如何挑战它的问题。在不断扩张的跨性别主义伦理道德中,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变得愈加迫切的原因在于跨性别意识形态和实践提倡将个体的「性别身份认同(gender identity)」和出生时的生理性别进行切割。
在新一轮跨性别主义浪潮中社会性别被纳入生物学范畴。跨性别支持者否认社会性别由社会文化和政治构建,声称社会性别,不论是否接受荷尔蒙治疗和/或手术,是依赖主观宣称界定身份认同的私人议题,仿佛是一个可以随意拨动的生物学开关。社会性别并非跨性别倡导者宣称的「自然力量」,相反它能被塑造成任何适应父权统治的样貌,这恰恰是跨性别意识形态在所有领域和机构迅速蔓延渗透的现状。
回望1979年,我曾预言那些为成年变性者提供治疗的大学附属医院的社会性别身份认同中心将不断扩张,最终演变成对不符合传统生理性别角色的儿童实施生理性别角色控制的中心。我在书中写道:「这样的社会性别身份认同中心已被用于治疗被标记为变性者的患儿」。如今一份最常引用的数据是: 在美国有六十多家治疗儿童「社会性别痛苦(gender dysphoria)」的社会性别身份认同诊所。然而社会性别地图项目3近期对这一数据提出质疑,该项目于2021年确认,北美地区现有超三百个社会性别身份认同诊所,其中多数位于美国境内 (The Gender Map,2021)。
当下对儿童跨性别医疗化是场人尽皆知的丑闻。目前寻求变性或跨性别治疗的患儿大多是女孩。根据社会性别身份认同诊所中主导儿童治疗的医疗模式,有问题的青春期阻断剂和异性荷尔蒙不出所料地被照单全收,医学界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异议。
好消息是,比起男孩,许多接受跨性别治疗的女孩正进行去跨性别(de-transitioning)并成为跨性别主义的批评者。
声明自我性别身份认同已然成为坚称自己是女性的男性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他们在呼吁推动跨性别立法运动。他们的口号是:如果你自我认同为女性,你就应该被视作女性,或者直截了当地说「男人可以成为女人」。我曾在《变性帝国》名为「手术打造的萨芙(Sappho by Surgery)」一章中提到,坚称自己是女性的男性也会宣布自己是「跨性别女同性恋者」。
在动笔前我曾反复斟酌,心知本书问世后跨性别支持者会再次如群蜂般兴奋地攻击我,只是这次会更尖刻毒辣。我不得不补上当前跨性别运动的最新议题,意识形态和实践,并不是说针对我的仇恨邮件和内容审查会就此打住,而是因为此前我已转而研究其他占据我思考,时间和写作的女性议题。
本书不是《变性帝国》的续篇,诚然没有第一本就无法写出第二本,不过它将注意力更多投向正在经历跨性别转变和去跨性别的女孩和女性们,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投身变性主义并接受荷尔蒙和手术治疗的女性非常少。
本书同样关注在 LGBT+ 社群中遭受性暴力的年轻女性。作为跨性别运动对女性暴力的幸存者,她们选择公开自己遭受的伤害,勇敢面对并顶住了跨性别社区普遍存在的针对女性性剥削问题的审查和噤声。这些暴力行为被主流 LGBT+ 组织刻意无视和压制,他们只关注那些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男性所经历的暴力。
本书将探讨个体幻觉的生物学化,例如跨性别群体痴迷于男性能经历月经,怀孕和哺乳等女性特有的身体经历。最后,本书还涉及跨性别新话 (trans newspeak)4,即跨性别群体试图剥夺我们的女性身份,却将女性一词留给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男性,将生理女性重新定义为顺性别女性、来月经者和前洞。
我的个人经历
我或许是第一位被正式命名为 TERF (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 的人,一个由所有跨性别批判者和废除主义者共享的污名称呼。
随着互联兴起跨性别活动人士逐渐脱离道德约束,他们在线上夺取话语权的同时肆意发表仇恨言论,给所有批判跨性别的个体打上恐跨症 (transphobic)的标签,指责他们拒绝接受跨性别信条,即男人能变成女人,的行为是仇恨犯罪。言论审查成为跨性别活动人士用来针对女权主义跨性别批判者的首选手段,和任何出于良知对跨性别信条持不同意见的心理咨询师、研究人员,或记者。
直到跨性别活动人士猛烈攻击那些对跨性别主义发表温和批判的男性批评者,这才稍稍唤起公众对激进女权主义者长年经历的厌女、网络喷子的恐吓和禁言的一点觉知和关注。当杰西·辛格尔于 2016 年为《纽约》杂志撰写文章时,作家朱利安·维果联系到他询问他是否遇到骚扰。「我是男性,所以我只经历女性经历的一小部分骚扰。」近年来跨性别活动人士在推特上发起一场有针对性的造谣运动,辛格尔因此遭到严重的网络骚扰和暴力(Kay, 2021)。
对我而言来自跨性别群体的审查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还是名博士研究生,试图申请一笔资金来支持研究和撰写后来成为《变性帝国》的博士论文。一所著名的美国基金会联系到我,说我的申请已经获批接下来只需走些形式上的流程。由于该项资助的一项额外福利是为申请者提供健康保险,对方要求我预约一次体检,这是申请保险的标准流程之一 —— 这次体检由他们出资,我也很快完成了。几周后一位在该基金会工作并为我的申请背书的同事告知我,我所采访的一所著名大学的性别认同诊所的教授们投诉说,我的调查会威胁到他们的研究工作。这显然是夹枪带棒的恭维,不用说基金会取消了对我的资助。
1995年,一位自我认同为跨性别女性的男士联系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社,指责我「故意」在再版的《变性帝国》中删除首版前言。这位投诉者在信中指控我「学术不端」,这项荒诞的指控称1994年版并非原版的如实复刻。出版社编辑回应称,删去1979版原序言是他们的决定,目的是将书籍控制在固定页数范围以便加入一篇新引言。
眼见编辑们不为所动,这位跨性别指控者又联系我的大学重申荒谬的「学术不端」指控,并要求开展纪律听证会证实对我提出的牵强指控。一位院长通知我,大学将对我进行调查,我反驳说出版商已完成调查并一应承担删去首版前言的所有责任。我补充说,如果大学执意对无理取闹的指控进行多余的调查,我将被迫寻求法律援助。院长听闻迅速改变主意,并给这位跨性别指控者回信表示「此类观点的适当表达渠道不是纪律听证会 …… 而是学界自由讨论和辩论的平台」。
同一时期我经历了由跨性别活动人士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抗议活动,地点在纽约市一家女权主义书店,彼时我正为另一本关于新生殖技术的著作举办发布会,抗议者如同几道严阵以待的关卡堵在现场,这令我在进出书店时感到极度威胁。此后,无论我在哪发言都会遇到大量类似的抗议活动。随着互联网兴起,针对任何质疑跨性别教义人士的恶毒污秽言论迅速蔓延,我开始收到大量恶意邮件。
在和跨性别主义唱反调的四十余年后,我得知自己任教二十八年的女性研究项目(现已更名为女性、社会性别和性学研究)在其官网上发布通告:
鉴于排跨激进女权主义在历史上的持续影响 —— 包括其在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女性研究历史的存在,为响应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和先锋谷跨性别社区就该问题的澄清请求,我们 …… 坚决反对我们学科,系和校园中的一切恐跨行为。
尽管已在2002年从大学退休,这份对我在系里的不明确存在而发的道歉声明让我感觉像是一个异端终于等到迟来的死刑宣判。「排跨激进女权主义者」一词或因法律原因未被正式命名,但显而易见的是,该系历史上除了我没有人和激进女权主义有一丝关联,或进行任何挑战变性主义与跨性别主义的神圣教义的研究和写作。
正如人们所说,余下的都成了历史,一段无论我在何处发声都遭遇系统性噤声并多次接到针对我个人的网络暴力威胁的历史。遗憾的是,这些对任何不认同跨性别教义 —— 即男人通过手术、荷尔蒙治疗或自我认同就能变成女人 —— 的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批评者而言并不新鲜。
跨性别话语体系、术语、缩略词及主张
跨性别话语体系包括术前和术后跨性别者、易装者、自称(社会)性别非二元、展示任何自认为是在跨越生理性别的身份或行为的人,以及仅「感觉」自己是异性别的人。他们中的部分寻求荷尔蒙治疗,通过外科手术改变外表,其余选择只改变着装和人称代词。
在一个被大众娱乐和虚拟现实幻想淹没社会中,将男性变为女性、将女性变成男性的虚构逐渐变成「现实」。英国记者海伦·乔伊斯指出,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的人口估算值很小,其中还可能包括一些「临时易装者」,乔伊斯强调,其中绝大多数未进行任何身体改变,也未经历所谓的社会性别痛苦(Joyce, 2020)。
当你有机会接触「缩略词社群」的内部人士就会发现,他们使用层出不穷的词汇和缩写作为身份标识,例如,AFAB (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与其相对的 AMAB (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5。又比如 LGBTQQIAAP,许多人已经知道 LGBT 是什么意思,QQIAAPP指:Queer 酷儿 、Questioning 性别身份质疑者、Intersex 间性、Allies 盟友、Asexual 无性恋、Pansexual 泛性恋 —— 以及其他当下流行的缩写。对使用者而言这些缩略词是一种政治声明,表明他们不愿被限定在「二元的」结构中或仅根据性取向被定义。当然,还有那个充满敌意的缩略词 TERF。
有时我会将「社会性别(gender)」和「跨性别(transgender)」相互替代使用。在希拉·杰弗里斯富有洞察力的著作《性别之痛(Gender Hurts)》中,她溯源了女权主义对社会性别的理解及其被颠覆的历史。在社会性别一词被广泛使用之前,『 更常用来描述此类社会构建特征的术语是「生理性别角色(sex-role)」』(Jeffreys, 2014),这也是我在早期变性主义著作中使用的术语。
杰弗里斯指出,「生理性别角色」一词不像「社会性别」那样易受腐化侵蚀,也未被跨性别活动家如此有效地利用和操控。渐渐地女权主义者将「社会性别」的内涵逐渐扩展,不仅包含社会构建行为还涵盖「男性权力系统及女性从属地位本身」,这一体系被称为「社会性别等级」或「社会性别秩序」(Jeffreys, 2014)。
随着「男性统治」和「女性从属」等术语逐渐过时,压迫女性的主体也随之隐身,仿佛提及男性,尤其以女性形象出现的男性是不礼貌的。杰弗里斯在书中写道,委婉表达的「社会性别」正彻底抹除男性对女性施暴的施害者角色,它同样抹除「针对女性的暴力(violence against women)」这一术语,如今针对女性的暴力通常被称为「基于社会性别的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这使得官方文件和表格中的「生理性别」被替换为「社会性别」,正如杰弗里斯指出的『仿佛「社会性别」本身是个生物学概念 』。
跨性别话语中还有其他一些词汇,其中侮辱女性的部分已被主流媒体采用。「顺性别女性」指天生女性,但极端跨性别者甚至不愿承认女性就是女性,仿佛只有自我宣称为女性的男性才能不加任何修饰地称自己为「女性」。此外,跨性别词典还充斥着许多冒犯女性的称呼,比如「来月经的人」、「有前洞的人」,以及我最喜欢的 ——「非男性」。
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类似词汇被用来形容男性。我很少听到顺性别男性这个词,更未听过「有后洞的人」或「非女性」这样的词。更不存在类似TERM (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Male) 这类用于标记排跨激进男性的缩略词。
在进步论坛里,参与者通过明确自己偏好的人称代词进行身份认同已然成为政治正确的做法。每个人都可以从一个不断变化的性别偏好代词或中性代词(PGPs)列表中选择自己认可的代词,例如单数的he、she、they、ze 或 zie6,正如论坛的一条指导原则所述,『绝对不要用 it 或 he-she 称呼某人,除非对方明确要求你这样做 』。甚至大学校长们也在签署信函时注明自己偏好的人称代词。奥斯卡·王尔德若在,或许会调侃说选择人称代词唤起了这些人的「词汇性兴奋(lexically aroused)」。
「使用死名(deadnaming)」7意味着我们不得提及任何个体跨性别前的生活。称呼死名几乎等同于犯罪,理应受到跨性别激进分子最恶毒的谩骂。如果你胆敢把完成性别转变的「她」称为过去的「他」,特别是如果你故意以这种方式表明任何「他」都无法成为「她」那你就犯了「误用性别代词(misgendering)」罪。令人头晕目眩是不是?而我以前还是名英语老师!
尽管许多人明白自称女性的跨性别者与天生女性并不完全相同,依然选择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这些,因为他们害怕被称为「TERF、拒绝接受跨性别群体存在的偏执者,或跨性别群体的迫害者」。许多人曾在各类论坛或通过电子邮件等私下场合向我表达这种恐惧「我钦佩您的勇气」,随后坦言自己无法公开挑战跨性别意识形态是因为害怕被贴上恐跨症(transphobia)的标签进而失去一切。越来越多的个体和机构开始将跨性别人士对批评者 —— 尤其对女权主义者的威胁和骚扰视为正常现象。正是他们将激进女权主义的反对立场污名化为「恐跨症」的行为支持了跨性别运动的宣传攻势。
我一直对「恐惧症」一词持批判态度,虽然它被定义为对某些事物或情境的非理性或持续恐惧,却经常被滥用在表达对特定群体的仇恨。对跨性别主义的激进批判者并不惧怕自我认同为跨性别的群体,更不憎恨他们。正如作家苏珊·摩尔明确指出的,「我们害怕的始终是同一件事:男性暴力,无论它被披上怎样的外衣。我们害怕失去生计;我们害怕身为女性已变成一种令人恐惧处境,以至于一些年轻女性不得不依赖药物摆脱它」(Moore, 2020)。
我们真正憎恶的是那些自称女性及其盟友对拒绝跨性别意识形态和不受欢迎的性骚扰的女性所施加的暴力。
「恐跨症」一词很容易成为攻击他人的标签,且一旦贴上难以摘下。一个人被贴上恐跨的标签似乎和被称为种族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一样恶劣。当这个标签使人变得畏惧而不敢表达真实想法时,受害者的就不仅是个体还有整个制度:制度因此获得贬低女性的正当性,政府因此被鼓励起草和通过那些将社会性别暴政合法化并抹除女性权利的法律。许多人想要对此保持无知,但这种无知并非出于天真,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不去了解的无知。
在讨论跨性别问题时总有一些聪明人提醒我们,要区分极端跨性别者和所谓绝大多数并不参与攻击女性的跨性别者,我总觉得这种行为居高临下。它让我想到女权主义者因谈论厌女症而多次受到责备的情形中同样有人坚称:「不是所有男性都厌女」,或直接指责我们憎恨男性,而事实是男性在憎恨女性。
批判社会性别的女权主义者们深知,跨性别群体并非思想统一且无内部分化的一块钢板。当然,厌女的跨性别者不代表所有跨性别者的观点。确实有部分跨性别者及其盟友—— 尽管数量远远不足 —— 对群体内部的厌女行为进行批判。然而跨性别者对女性和女同性恋者的网络和现实攻击日益增多,而跨性别意识形态的演变不断为这些攻击提供正当性,这些现象逐渐成为跨性别运动的目标所在。
要保持礼貌吗?
人们常说使用跨性别者自己选择的代词只出于礼貌。记者和教授罗伯特·詹森报告称,当他与给出这类理由的人们的谈话时,他们都小心翼翼避免伤害跨性别者的情感。「对他人保持敏感是合理的,但这种敏感是否应当凌驾于理解问题的尝试之上?对这些议题避而不谈是否真的尊重跨性别者 …… 这种行为是否基于一种假设,即跨性别群体没有足够的情绪能力来面对自己提出的知识性与和政治性主张? (Jensen, 2016)
我既不用「她」称呼自称女性的个体,也不用「他」称呼自称男性的个体。我不认为使用一个对方本不属于的身份称呼是礼貌的。即便瑞秋·多莱扎尔8,一位坚称自己是黑人的美国白人女性,希望被这样称呼,我也不会称一个白人为黑人。
跨性别冲突涉及的内容远超个体「感受」,这种反女性和反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对立法产生深远影响,在将男人可以成为女人的权利合法化的过程中丝毫不考虑那些可能因该立法受到伤害的女性的意见。不幸的是,在跨性别立法被提上议程的地方,公众舆论往往滞后于公共政策
我们被愈加频繁地要求称男性为女性,称女性为男性,来使语言使用符合跨性别群体要求。然而当跨性别意识形态渗透进司法体系,尤其在有证据表明跨性别支持组织正逐步干预法院代词政策的起草工作,代词问题就不再是礼貌问题。2020 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发布一项庭审指导,规定所有出庭人员都要在庭声明希望他人称呼自己的代词。「根据这项政策,在法庭上自我介绍时无论外表是否符合其生理性别均必须声明自己的代词」。如果出庭者未主动说明 「我的代词是……」,书记员或法官会提示其遵守这项规定(Litzcke, 2021)。
这项政策据称要促进「包容行为」,但听上去更像是「强制行为」。实际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律师协会事先并未被征求意见,只有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委员会(SOGIC)的一组律师参与代词政策起草工作。法院「在 SOGIC 的帮助下完成这项政策的制定」,随后 SOGIC 成为该政策和法院的公关代表。当该省法院首席大法官被追问该政策带来的影响时,她回答说提问者应该向 SOGIC 寻求答案 。
正如记者卡琳·利茨克指出的:「法官不止一次地用男性代词称呼那些处于性别转变审核程序中的女孩,而她们是否能进行性别转变本身正是案件审理内容。如果法官的语言本身就预设结果那又何必走一遍司法程流程呢?」。这些变化发生在一个更广泛的司法判决背景下,法院在多起案件中而不顾当事人父母的反对意见作,出支持希望接受变性手术的未成年人的裁决。这引发了一个问题:「法院是否正被某种意识形态运动裹挟,以至于该运动的主张已经凌驾于法律原则之上?」
在纽约市,企业或雇主故意且重复地对跨性别员工「使用错误代词」或面临高达25万美元的罚款。然而你却能故意且重复地称一个女性为「贱人」或「婊子」而不会被视为发表真正的仇恨言论。
安大略省人权委员会于2014年通过一项政策,规定「在《人权法典》涵盖的社会领域内(包括就业、住房和教育等服务),如果拒绝使用跨性别者选择的名字和与其性别认同相符的人称代词,或故意错误称性别,很可能构成歧视」(Ontario Human Rights, 2014)。
然而当被错误地称呼为「顺性别女性」、「来月经的人」、「有前洞的人」、「有子宫颈的人」和「非男性」时,我们却从未获得主张遭受歧视的权利。我们呼吁的是一种未经重新定义的女权主义9,正如凯瑟琳·麦金农在1987年写的,「未经重新定义的女权主义」必须建立在「未经重新定义的女性」,即拒绝被男性定义的女性的基础之上。
进步组织中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男性遭遇的暴力受到广泛关注,这并不奇怪,因为男性问题,从男性运动到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男性通常占据大量公众注意力和资源,而女性问题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背景板中。同样的,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男性现在正在占据女性历史的首要地位。
针对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的暴力
当我告诉一位同事,我正撰写一章关于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面临的男性暴力的书稿时,她以为我指的是针对自我认同为女性的跨性别者(男性)的暴力。这位同事是一间家暴中心的工作人员,她帮助的跨性别受害者大多是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男性。她在工作中目睹自我认同为女性的跨性别者(男性)遭受严重暴力,但我从未听她提及任何自我认同为「跨性别男性」的女性经历的暴力和困境。
近五年来,美国人权运动委员会(HRC)一直追踪并报告「致命的反跨性别暴力 」。然而这些报告只记录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男性跨性别者遭受的暴力,并未统计自我认同为男性的女性跨性别者遭受的暴力和性剥削。2020年,HRC 的报告记录了三十七名跨性别或「性别非二元」个体被害案,受害者大多是黑人和拉丁裔的跨性别者(男性)。我怀疑,针对自我认同为男性或性别非二元的女性施暴是敏感话题,因为此类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很可能是活跃在 LGBT+ 相关团体中的跨性别或性别非二元男性。
在奥勒冈州波特兰市,记者莫妮卡·罗伯茨曾就自己所在社区的跨性别谋杀案开展调查「究竟是谁在杀害这些女性,又是为什么?」佩奇·克雷斯曼,一位当地自我认同为女性的政治组织者发现,这些谋杀案并非由成群结队的法西斯分子四处搜寻跨性别女性进行随机仇恨犯罪,而是「据统计数据显示,最常见的施暴者是跨性别女性的亲密伴侣…… 行凶者通常知道他们的伴侣是跨性别者;声称暴力和谋杀出于对跨性别的恐慌是他们逃避承认明知对方是男性但仍对其产生性吸引的事实」。克雷斯曼认识的大多数「跨性别女性」被杀害时,凶手都清楚知道他们是跨性别者。
在通读这篇波特兰的新闻和HRC的报告时,我很想知道HRC是否承认针对自我认同为男性的女性的暴力行为事实存在。我浏览了HRC官网,还翻阅了该组织的早期报告,一无所获。我对「跨性别男性」遭受的暴力进行有限调查,却找不到任何提及此类暴力的新闻和报告,但针对「跨性别女性」暴力的文章和报告却频频出现。
在一些批判社会性别博客的帮助下,我发现一些对女性发出恶毒言论和暴力威胁的网页,部分受害者是女同性恋者、不符合社会性别规范,以及自我认同为跨性别男性的女性。一位女同性恋活动人士向我展示了一大批曾活跃在 LGBT+ 社群的女性的证词,她们都指出 LGBT+ 社区存在对女性的严重性剥削,其中大部分由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男性、跨性别女同性恋者、性别酷儿,或性别非二元男性所为。需要补充的是,对女性的性剥削涉及强奸、性侵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这位活动人士作为男性暴力的幸存者向我讲述了男性暴力如何在 LGBT+ 圈子中持续存在。
许多男性暴力的幸存者在近期出版的书籍《你告诉我你是不同的:伤害文集(You Told Me You Were Different: An Anthology of Harm)》中勇敢公开她们的经历。
针对女性的暴力由 LGBT+ 团体中部分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男性所为或许是我们很少听闻这类报道原因之一,也回答了为什么人权运动委员会等组织始终对此避而不谈。
由自我认同为女性或性别非二元男性施加的男性暴力是跨性别运动的肮脏秘密。在这个秘密中女性的证词受被沉默守则10(code of omertà)压制 —— 一种禁令性的沉默文化,要求群体成员不得泄露「兄弟们」的秘密。
这些经历男性暴力的幸存者们报告说,打破沉默守则的女性受害者无一例外地遭到围猎,如果她们胆敢谈及自己遭遇的暴力会被立即指责为「助长跨性别女性有威胁的谣传」。这些女性受害者还被告知「即使这是真的 …… 你也不该说出来 」(Kitty Robinson, 2021),这是对道德责任的公然放弃。这些群体中针对女性的系统性暴力被一种为暴力行为开脱的「强奸辩护论」11所篡改。
在《你告诉我你是不同的》一书中,主编写到「这种强大的噤声策略让我们许多人长期保持沉默并深陷其中 」。她还提到,女性受害者披露真相会被指控为「杀害跨性别女性」,要为所有自我认同为女性的跨性别者的死亡负责。「当一位遭受男性跨性别者侵害的女性认为男性跨性别者是地球上最饱受污名和压迫,最易遭受侵害的群体时,对自己遭受的暴力保持沉默是唯一的道德良选 」。
【让遭受男性暴力的女性幸存者发声更有力】
在当下进行性别转变的群体中,希望成为跨性别男性的年轻女孩数量呈上升趋势。然而,放弃跨性别身份(desist)和去性别转变(detransition)最多的同样是这些女孩和年轻女性 —— 她们中许多人用感人至深的文字讲述这段经历。在各类线上平台以及一些问世的书中,过去自我认同为「跨性别男性」的女性动情地讲述了这段与自我、与其他女性的连结断裂的过程;她们如何逃离被强加的女性特质;她们遭受的性虐待和侵犯;她们在厌女文化中成长的痛苦经历;她们也记录了重新恢复女性身份的旅程(Max Robinson, 2021)。
正如 #MeToo运动使男性开始为其对女性的虐待和侵害行为负责一样,有原则的人有责任让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群体为其恶劣行为负责。部分跨性别女性明确表明他们不是女性,主动和社群中大多数人宣称的女性身份划清界限。不幸的是,这些行为无法改变另一事实:仍有数量相当的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男性及其盟友用极其恶毒语言攻击女性,企图通过将「女性」一词从任何以「 女性」为标题或使命的团体或组织中删除的方法抹除「女性」这一概念。
本书的目标之一是让那些受到跨性别双重思想伤害的女性幸存者们更有力地发声,并将她们认定为男性性暴力幸存者 —— 这些女性中许多曾自我认同为跨性别男性、性别非二元或酷儿。
那些遭受性剥削、强暴与侵犯的女性幸存者的证词,在诸如女权主义反人口贩运运动和废除卖淫制度的运动中一直起着关键作用。对于揭示跨性别意识形态、相关实践乃至直接性暴力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幸存者的声音具有无可替代的权威性。
在未被审查的情形下,那些呈现女性幸存者经验的网站、博客、新闻发布和文章,在推动公众认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书写与倡议,那些遭受跨性别暴力的幸存者揭示了跨性别产业的真实面貌。她们比任何人都更有能力揭开这一正在严重危害女性与儿童的产业所制造的神话面纱。如今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开始以个人或集体名义发声,公开质疑跨性别话语体系中的正统信条。
【本书使用的语言】
在探讨用来称呼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者的措辞时,我不想成为和跨性别代词警察一样的语言专制者。在《变性帝国》一书中我创造了「男性到构建的女性(male-to-constructed female」这一术语来揭示跨性别身份的虚构性。尽管这个术语在表达上具备真实价值,但它在实际使用中却略显笨拙,无论是说出口还是在键盘上敲下都不够流畅自然。
在书中的某些段落我选择使用「转变者」、「自我认同为跨性别男性或女性」、「男性身体的女性(male-bodied female)」,或「女性身体的男性(female-bodied male)」等术语,并根据具体语境判断哪个术语更能清晰表达内容。在其他一些生理性别不甚明确的地方我会在括号中注明该人的出生性别,例如「自我认同为女性的跨性别者(男性)」
我极少使用「跨性别者」、「跨性别女性」或 「跨性别男性」这些术语,因为它们暗示性别过渡是从一种生理性别到另一种生理性别的真实转变。它们被发明的目的是推动跨性别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因此只有在引用他人作品时我会使用这些术语。此外,由于大多数人仍然使用这些术语,我也会在某些情况下保留它们减少混淆。
我个人更倾向使用「自称女性(self-declared woman)」或「自称男性(self-declared man)」等具备批判性诚实的术语,它们对跨性别者声称「出生在错误的身体」的说法提出质疑,且能更清楚地描述跨性别转变中的自我认同过程。如需使用较长表述,我会使用「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男性」。不过不必担心,如果某人出于某种原因选择使用其他术语,我也不会「误称」它们。
此外,在本书中我还会使用「社会性别批判」,「社会性别废除主义者」,「社会性别不符(gender non-conforming)」,「不遵循社会性别规范(gender non-compliant)」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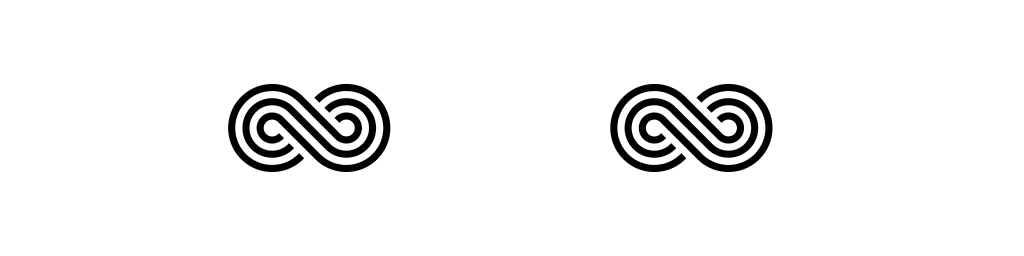
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将大洋洲对语言的操控称为「新话(newspeak)」并全面推广,「新话」是「双重思想(doublethink)」的基础。小说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解释说:「双重思想意味着在头脑中同时持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 一边故意撒谎,一边真诚地相信那些谎言…… 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如今许多既相信又不相信跨性别教义的人正处于相似境地:他们面对一种扭曲现实的语言以及一个维系这种语言的社会性别产业时就会陷入双重思想的困境。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图书馆、大学等公共机构开展一次建立在真实和知识基础上的公开对话,而是选择妖魔化激进女权主义批评者和其他不愿屈从去跨性别「新话」的人?当跨性别意识形态的异见者还未开口就被贴上「恐跨」标签,或被那些本应鼓励言论自由的公共机构审查和噤声时,双方无法展开任何对话。跨性别运动的激进支持者似乎害怕辩论。
鼓励批判性思维是出版商的职责之一,可为什么出版商迟迟不愿出版批评跨性别主义的文章和书籍?美国的出版记录显示批评跨性别主义的作品很少进入商业图书市场和主流媒体,甚至在进步电子期刊和大学图书市场中也鲜有出现。结果便是读者难以了解跨性别意识形态及相关议题的实质反对声音,和伴随而来的虐待、骚扰和暴力现象,更无法意识到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自我声明其生理性别将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
由于跨性别活动人士主要争取自我认同为女性的男性权利,因此跨性别运动很大程度上在迅速成为更大范围男性权利运动的一部分。跨性别女同性恋者不断将拒绝其性邀约的女同性恋者妖魔化的行为和「非自愿单身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由不满现状的单身男性组成,他们将没有约会对象的状态称为「非自愿禁欲」,这也是最危险的网络邪教文化之一。
跨性别主义并未在广大公众中得到充分理解。很少有人了解手术「性别重置手术」究竟涉及什么,更少有人知道当下儿童跨性别的发展情况,其中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在性别认同诊所接受所谓的性别焦虑治疗,在青春期前被迫使用青春期阻断剂,并被鼓励进入青春期后接受荷尔蒙治疗。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围绕那些声称自己「被生在错误身体」的儿童进行医学干预的问题,正在国际上引发激烈争论。
旁观者可能会对那些在性别认同上挣扎的青少年产生真切的关切,有些人甚至相信跨性别宣传话术 —— 只有通过医学干预才能拯救这些青少年,避免他们走向如自杀等更糟的结局。但他们并不了解一个失控的跨性别主义意识形态与产业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普通公众也无法理解性别身份自我认同合法化带来的代价。许多家长不知道,孩就读学校的课程正在「认可」孩子的新性别认同,甚至在未征得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协助孩子接受荷尔蒙治疗。
在本书中,我试图呈现跨性别议题中许多人尚不了解的若干侧面。我猜想大多数人并不会阅读那些关注此类议题的各类博客。虽然女权主义者以及长期以来反对跨性别正统观念的人可能早已熟悉本书中的许多内容,但我们仍有必要将女权主义批判的核心内容传播得更广泛,让更多人理解这场冲突中的真正利害关系。
译者注:
- 前洞(front holes):通常被跨性别活动人士用来指代天然女性,将女性物化为生殖器并将其简化为一个无意义的洞,来实现对女性身份的贬低、盗取和剥夺。 ↩︎
- 译者注:为避免混淆,本书所有的 sex 译为生理性别,所有的 gender 译为社会性别。 ↩︎
- 社会性别地图项目(The Gender Map):由女权主义运动团体 —— 妇女解放前线(Women’s Liberation Front)发起的在谷歌地图上标注并分享所有性别诊所,包括儿童性别诊所的运动。随后该项目在跨性别团体的抗议下被谷歌地图下架,Gender Map主页也被其搭建平台WIX.com关闭。 ↩︎
- 新话 (newspeak):出自乔治·奥威尔小说《1984》,指通过控制和重构语言来限制思想、操纵现实的极权语言体系。 ↩︎
- AFAB = Assigned Female At Birth 即出生时被指定为女性;AMAB = Assigned Male At Birth 即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 ↩︎
- ze 和 zie是中性代词,用于替代传统的 he 和 she 来表达非二元的性别认同。 ↩︎
- 使用死名(deadnaming)指使用跨性别个体在性别转换后不再使用的出生名字。按照跨性别社区的解释,这个行为忽视了跨性别个体的性别认同和他们所选择的新名字,会引起他们情感痛苦或不适。 ↩︎
- 瑞秋·多莱扎尔(Rachel Dolezal),更名为恩凯奇·阿玛雷·迪亚洛 (Nkechi Amare Diallo) 是美国前大学讲师和活动家,尽管父母都是白人,但她坚持认为自己是黑人并成为前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分会主席。这一风波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种族身份的全国性辩论,批评者称她文化挪用和身份欺诈;多莱扎尔则坚称她的自我认同是真实的。 ↩︎
- 未被重新定义的女权主义(Feminism Unmodified) 指不受被自由主义或其他意识形态重新定义或改写激进女性主义;未被重新定义的女性(Females unmodified)强调女性必须保留其生理女性身份,拒绝被男性或跨性别意识形态重新定义。 ↩︎
- 沉默守则,也称奥梅塔守则(code of omertà):源自意大利黑手党的行为准则,即保持沉默,不得泄露内部事务或成员的秘密,即使在面对外部调查或压力时也不会打破这一守则。 ↩︎
- 强奸辩护论(rape apologism),指的是试图为强奸行为找借口,辩护,将责任推给受害者来减轻其严重性的行为或观点。 ↩︎
- gender non-conforming 指不符合传统性别角色或性别表达的人,他们会表现出与其生理性别不一致的行为或特质;gender non-compliant 指的是不遵循性别规范或性别期望的人,他们会拒绝社会对于特定生理性别的期望或行为标准。 ↩︎

发表回复